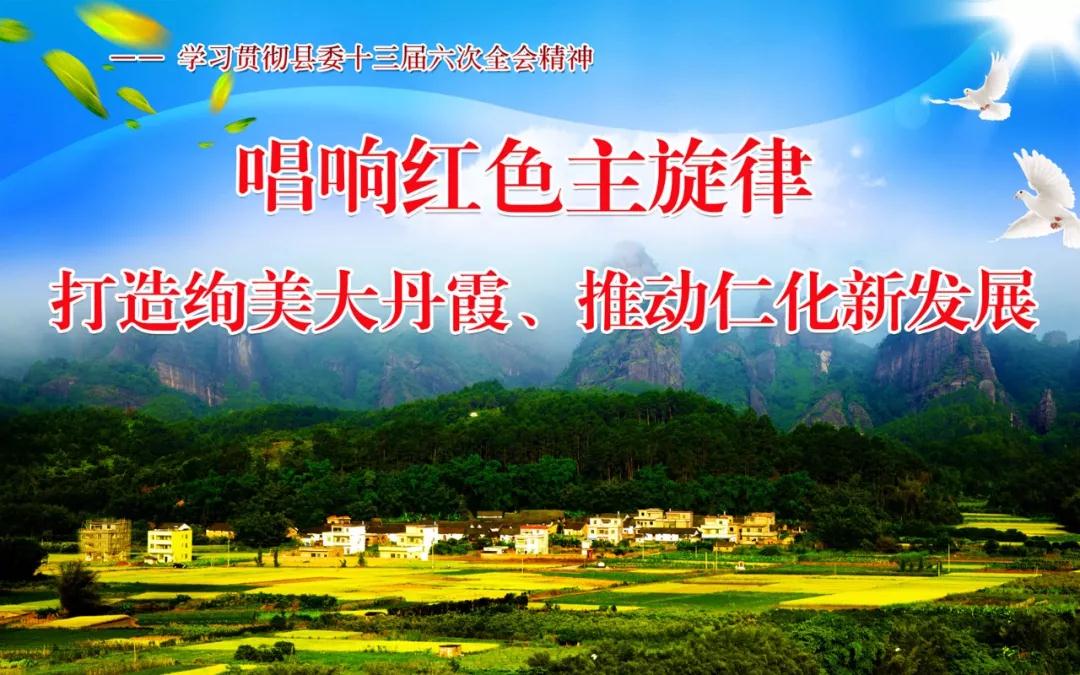
虎口拔牙襲城口,血染錦水戰銅鼓
——民國檔案真實記載紅軍長征突破
仁化第二道碉堡封鎖線
徐誠林 劉耀東 謝紀根
鴻雁哀愁驚冷月,杜鵑泣血漫山紅。
粵北仁化是千年古城,是紅軍長征突破國民黨第二道碉堡封鎖線的主戰場,鮮有史學家的濃墨重彩,今天翻開塵封的檔案,依稀可見國民黨軍的前堵后追,可聞當年的烽火硝煙……湘粵贛邊陲的古城仁化,在紅軍長征生死存亡的關頭,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。
1934年10月下旬,紅一方面軍突破國民黨第一道封鎖線后,1934年11月初,毛澤東隨軍委縱隊到城口。當時,毛澤東身患瘧疾大病初愈,身體十分虛弱。雖然他沒有任何軍事指揮權,但只要隊伍停下來宿營或休息,便對著地圖仔細研究,毛澤東分析當時的軍事情況,認為在紅軍向西的道路上,必會有國民黨中央軍、湘軍、廣西軍閥的部隊等敵人的重兵阻截。毛澤東鄭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議:“紅軍不要向文明司前進,不要在坪石過粵漢鐵路,不要奪取宜章、臨武,而應該向北越諸廣山,沿耒水北上,在水口山一帶休整,仍回到永豐、藍田、寶慶等地擺開戰場,消滅‘圍剿’之敵”。毛澤東的計劃是紅軍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。毛澤東的這一建議在城口沒有被采納。
其間,紅一、九軍團和紅三、五、八軍團各一部在位于贛、粵、湘邊的仁化縣境內行軍作戰10余天,甩掉了國民黨的追擊和堵截,進行了奇襲城口鎮和銅鼓嶺阻擊戰,摧毀國民黨設在仁化縣境內的碉堡26座,突破了國民黨設在廣東城口至湖南汝城、桂東間的第二道碉堡封鎖線,穿越了仁化縣山區長江、城口、紅山等地。
一、奇襲城口鎮
半卷紅旗臨易水,霜重鼓寒聲不起。
城口是湘粵邊境的秦漢古鎮,東臨東河,西連西河,東西河匯合于城南,成半島狀,城北依托羊牯坳,四面群山環抱,山峰陡峻,谷狹路隘,地勢險要,扼粵湘驛道之咽喉,控南北商賈之要隘,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。蔣介石多年苦心經營,強化鄉里制度,清查戶口,處理食鹽,堅壁清野,決意把城口建成堵截紅軍第二道碉堡封鎖線南端的中心據點。四周高山構筑有碉堡20多座,密布成網,扼守著峽谷、道路口,可瞭望和控制仁化、扶溪、長江、汝城、延壽、樂昌方向來路。碉堡間溝壕相連,電話相通。東水橋、七星橋、河背橋及門樓設有哨所,配有哨兵。鎮內駐有國民黨軍獨立第三師李漢魂部一個連和部分民團固守。
1934年11月,紅軍突破國民黨軍設置的第二道封鎖線就是從襲擊城口鎮開始的。
擔任襲擊任務的是紅一軍團二師六團一營。紅一軍團首長林彪、聶榮臻、左權都清醒地認識到,城口這個隘口,是中央紅軍西進的唯一通道,必須乘敵不備、突襲智取,一舉成功。二師六團團長朱水秋、代政委王集成分析了城口敵情,認為守敵人數不多,但設防堅固,有精良武器和充足彈藥;若正面進攻,雖有取勝的把握,但要付出較大的代價,甚至會耽誤時間,影響軍團部戰略部署的完成。為此,將主攻城口的任務交給一營擔任,并把團的偵察排撥給一營指揮。一營營長曾保棠面臨的是一個艱巨任務:城口鎮內的守軍雖不強大,但要求他的營一晝夜奔襲220里,這無異于上天攬月,虎口拔牙。
十一月的山城,已是冰封凜冽,寒風嗖嗖。軍令如山,任務艱險,臨行囑托,字字千鈞。11月1日黃昏,一營出發了,序列是偵察排、機槍排,一連、二連,排成四路,疾速跑步前進。夜,伸手不見五指,踏著野草沒脛的山路,一不小心就可能葬身懸崖。天亮時候,趁在樹林吃早飯空隙,曾保棠在地圖上一量,發現這一夜竟然跑了150多里。本打算讓部隊休息一下,但是根據行軍經驗,保棠知道,戰士們只要一躺下就會抵擋不住困意呼呼大睡。于是決定連續趕路,第二天黃昏來臨時,曾保棠看見了前面的城口鎮。
這是一個被幾條河渠環抱著的小鎮,鎮前有一座木橋,要想占領鎮子必須從橋上過去。曾保棠率領一營指戰員,乘著夜色潛伏到離橋頭百米處的草叢中匍伏著,先部署兩個連對付兩側的碉堡,又選擇十幾名水性好的戰士由橋的上游泅水過河,自己帶著偵察排強行過橋。敵哨兵發現異常,喝問是哪部分的。曾保棠響亮回答:“我們是中央軍!”并快步過橋。敵哨兵準備鳴槍示警時,已被紅軍撲倒,隨著一顆顆手榴彈在敵營棚里炸開,紅軍迅速過橋、入城,包圍敵軍連部及民團、保安駐所,“繳槍不殺”山鳴谷應,響切云霄,敵軍“有的還沒有見過紅軍,有的沒有想到紅軍來得這樣快”(《聶榮臻回憶錄》),紛紛舉手投降,紅軍戰士立即沖上,先將敵軍步槍扳機除去,讓士兵用籮筐挑走,隨即命令俘虜將槍支扎捆,背負集中。
附近五里山碉堡里的守軍發現有紅軍,就不斷用步槍、機槍向外射擊,有些紅軍戰士就在黑夜的冷槍中無聲的倒下了,對紅軍軍事行動傷害甚大。碉堡是用石及磚造成,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;大小不一,有排堡、連堡,十分堅固,易守難攻,紅軍迅速分多路包圍五里山碉堡里的敵軍,堡內敵軍見紅軍銳不可當,隨即潰不成軍,紛紛棄堡逃竄,紅軍迅速占領了城口鎮。
奇襲城口,紅軍俘敵100多人,繳獲槍械數百支、子彈一萬多發及糧食、煤油幾千箱等物資,給紅軍在城口短暫休整創造了條件。對此,中革軍委通電全軍:“我一軍團前鋒于2日經過戰斗已占領敵第二道封鎖線上重鎮城口,突破了敵人的封鎖。”(林偉《“戰略騎兵”的足跡》)
11月3日,紅一軍團令二師四團和六團一部在城口休整。蔣介石得悉第二道碉堡封鎖線南端重鎮城口失守,于4日令衡陽航空隊派轟炸機兩架,飛抵城口鎮上空。沒見過飛機的群眾,聽有飛機嗡嗡聲,出于好奇,好些人跑到曬坪、街頭、甚至登上陽臺觀看。敵機在五里山上空俯沖,用機槍掃射,被扼守在五里山頂碉堡、戰壕里的紅軍戰士開槍還擊后,又飛到三角坪、大河背、老虎尾、正隆街口等地轟炸。一顆炸彈落在正隆街保安堂和生泰店之間,震天巨響,房屋崩塌,煙硝、灰塵四起,人們哭叫。共炸毀6間房屋,炸死、炸傷10余人。紅軍戰士見狀,迅速行動,搶救受傷群眾,有的搬走瓦礫、磚頭,有的替傷者包扎、治療,群眾深受感動。
紅軍占領城口,就意味著徹底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。各軍團紛紛進行政治宣傳,如演講、畫漫畫、刷寫標語等,其中有紅五軍的“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”“打倒帝國主義”“農民起來打土豪分田地”……;獨立師訓練隊的“士兵不打士兵,窮人不打窮人”等標語布滿城口鎮的街頭巷尾,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紅軍西進的宗旨。紅九軍團經過城口時,已是夜色茫茫,大風呼呼,天氣異常寒冷。軍團部下令二十二師在后面,三師及軍團直屬隊在城口戰備休息。軍團部住在城口東端的敵人鎮公所漂亮寬大的房子里。據紅九軍團部文書林偉回憶,“我們在街上買到兩雙膠底鞋子,還買了一些辦公文具,黃參謀買了許多糯米和紅糖,正在做江西元宵,科里的人都圍繞火盆烤火吃東西,郭輝勉同志會按琴,他奏起了‘梅花三弄’的曲子……”
這樣的事,無疑是給紅軍艱苦的行軍戰斗生活增添了一些花絮,活躍了氣氛。堅定的信念、樂觀的精神,感染了身邊的人,又繼而傳播到更廣的人群中去,鼓舞了全體紅軍將士的斗志,振奮了所有行軍人員的精神。
二、血戰銅鼓嶺
爆炸轟鳴如擊鼓,槍彈呼嘯若琴彈。
銅鼓嶺位于城口鎮南面二十公里處,嶺高坡陡,林密草深,嶺下溝深陡峭,地勢復雜。從嶺腳到嶺頂,只有一條通道,路窄彎曲,是城口鎮通往仁化的要沖隘口。
正當紅軍由贛境挺進粵、湘境內的時候,國民黨獨立警衛旅第三團團長彭智芳,于10月30日受令于廣州,翌日率部乘粵漢路專列火車到達韶關,轉乘軍用汽車百輛,開拔仁化縣城,接著火速進軍,直撲高沙一帶,搶先在高沙村北、銅鼓嶺南麓集結兵力,占領高地,扼守山隘、路口,修工事,挖戰壕,準備乘勢北上,搶占城口鎮,企圖阻攔并消滅紅軍。
為確保紅軍主力在城口的短暫休整,順利西進,紅二師六團一部奉命從城口的東光、恩村迂回到銅鼓嶺北的山地,阻擊從廣州來增援城口的敵人。
……據練騁文急報,匪已節節推進,圖陷仁城,維時城內僅有縣兵30余名,我一面親督隊固守駱駝峰三關閣等處碉堡,一面奉令電商彭團趕赴前線追擊,詎甫抵厚坑,匪已間道包抄繞出我軍之后,幸團長彭智芳奮勇向前,血戰兩晝夜,殲敵千余,匪遂狼狽潰逃……(轉載自仁化縣檔案館藏民國檔案)
11月4日中午,紅一軍團二師六團一部遭到彭智芳部襲擊。敵人依仗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勢,用輕、重機槍、步槍瘋狂掃射,紅軍傷亡很大。但久經考驗和富于戰斗經驗的紅軍指戰員,面對突如其來的險惡形勢,隨機應戰,搶占有利地形,痛擊敵人。敵人雖有傷亡,但更兇猛頑強,自以為兵多彈足,重新聚集部署,分多路向紅軍陣地猛撲,在密集火力掩護下,跨出工事、戰壕,拼死命向紅軍陣地沖殺過來。紅軍指戰員沉著應戰,待敵人沖至陣前,一躍而起,揮舞著大刀,勇猛沖殺,與敵人展開白刃格斗。隨著震耳欲聾的喊殺聲,戰士們手起刀落,敵人一片片的倒下,陣地上尸橫遍野,戰士們渾身上下血跡斑斑。刺刀捅彎了,就用手掐、牙咬、拳打。紅軍指戰員士氣旺盛,愈戰愈勇,敵人一次次地進攻,又一次次地潰退,戰斗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。
雙方繼續激戰,戰至深夜,敵人的進攻有所減弱,紅二師六團一部完成了阻擊敵人的任務,便邊警戒,邊分批悄悄地往北方向轉移。轉移出陣地的紅軍隊伍,迂回到厚坑至恩村之間的岔口分道:一路在瑤塘山腰折向帶頭村,經官奢村向左坑進軍;一路在馬嶺橋經馬奢向新洞進軍。紅軍離開銅鼓嶺地域,敵獨立警衛旅彭智芳部怕紅軍有埋伏,不敢追擊,間續地向紅軍發射壯膽助威的槍聲,只圖自保,繼續扼守在銅鼓嶺山地。
銅鼓嶺阻擊戰打響后,城口勝一理發店和大坪頭交通站的地下黨,立即發動群眾,組織擔架隊,及時趕往作戰前線,搶救紅軍傷員,當地百姓踴躍參加支前工作,為紅軍燒水、送飯、通訊、帶路等重要任務,為這次戰斗的勝利做出了貢獻。
銅鼓嶺阻擊戰歷時兩晝一夜,國民黨粵軍軍傷亡80多人,紅軍陣亡140多人。山上那條狹小的隘路,遍地尸骸,戰斗時要踏著尸體前進,戰況的慘烈,由此可以想見。紅軍雖然損失較大,但遏制了敵人,將國民黨軍牢牢控制在銅鼓嶺南麓一線,掩護紅軍主力在城口短暫休整和安全通過城口一帶。
紅軍長征過境仁化10余天,播下了革命的種子,留下了長征精神,是仁化這片紅色熱土永恒的精神財富。
美麗的錦江河畔,洪流滾滾,那是紅軍隊伍在急行軍;
峰峰如劍的萬時山腳下,白雪皚皚,那是著紅軍長征駐扎的帳篷;
斑駁、殘缺的古秦城,莊嚴肅穆,那是歷史的記憶,流淌著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悲壯故事。
(縣史志辦)



